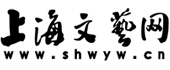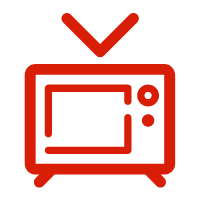說起來,我“認識”曹小航已有不短的一段時間了,但如同她的這首詩,如同她詩集的命名,感覺中她亦一直在我的一米之外,我能感受得到她掌心里的暖,卻又無法不迷失在她蒙娜麗莎的微笑。
我第一次“見”她,是在三年前,那年讀庫群里的女作者們一起過了個三八節(jié)。說是一起,其實是網(wǎng)絡上的,按主創(chuàng)的策劃,每人提供一張相片,下面寫上一段話,是作為法律人,對這個職業(yè)的感懷。十多個人的整理在一起,成了一篇公號文。
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曹小航,相片上的她穿了一件淡藍色的短上衣,肩上搭一款同色系長絲巾,整個人看上去大方得體,知性優(yōu)雅。透過簡介,知她來自上海,是個檢察官。
我們第一次交談,是在那一年以后的事了。那天,我發(fā)了一篇題為《一個女人的困境》的文章,是對電影《朗讀者》的影評,寫德國人對二戰(zhàn)進行反思的。她在文后留言贊了,又轉到群里,再贊。那之前很少見她在群里說話,那之后,我們成了朋友。
然而感覺中她一直在一米之外,對她的了解星星點點都是來自她的朋友圈,不時讀到她寫的詩,看到她參加的文學活動,知道檢察官之外,在全國檢察院系統(tǒng)和上海文壇,她還是個大家耳熟能詳?shù)脑娙恕?/div>
我們真正有交集,是在2018年9月以后的事。那天大概是9月的16或17日,我比較清楚地記得這日期,是因為那是幾個中國游客被瑞典警察扔在荒郊野外之后的事,我為此還留下過文字。
那一事件,當時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法律人中自然不會少了關注。我們群里法律精英居多,大家對自身要求嚴格,對那幾個游客多是恨鐵不成鋼,覺得瑞典人有自己的規(guī)則,他們自取其辱,也是自找難堪。
我則以為,對一個人的態(tài)度背后,是對一個國家的態(tài)度。何況異國他鄉(xiāng),深更半夜,荒郊野外,單是從人性上講,瑞典警察也太過分,對那幾個當事人我更多的是悲憫和同情。
我的看法和思維,常有些與眾人逆反,這好像骨子里天生的“異稟”,有朋友曾善意稱之為批判性思維,而照直說是有點不大會合群。又好直抒胸臆,就常引發(fā)一些辯論。在一個優(yōu)秀的群里,辯論其實是很讓人受益的,它會促進你的成長,但這過程中,常也不免覺得有點孤獨。
然而這一次不同,我很快就發(fā)現(xiàn),有人和我站在一起,那就是曹小航。她甚至比我還認真,比我更沖在前面,如果說那些朋友是在談別人的事,客觀,理性,小航爭得就有點感性,那一刻,她設身處地,那幾個人的遭遇和處境,似乎與她都是息息相關的。
過后我常常想起那晚,想起她那股近乎翻臉的有點孩子氣的認真勁,想象她爭得幾乎有點面紅耳赤的表情,感動之余總是不由嘴角微微上揚,在心里說:小航姐真是個詩人。
曹小航很善良,她的善良里甚至帶著一些單純和天真,讓人想到處子,想到初心。她對他人人生的那種悲憫和關懷,讓我相信,她對她的案件和當事人,會傾注滿腔的認真和謹慎,因為這,會最大限度地避免讓無辜者蒙冤。
然而,她是一名檢察官,首要的職責該是指控犯罪,作為一名公訴人,她是否太溫柔了?
盡管在《一米之外》里,她只著意“拯救”和“溫暖”,拒絕被“懂得”和“置疑”,然而我一直相信,讀一個人的書,可以了解一個人,因為,文字里有她(他)的靈魂。
帶著質疑和探尋,當我翻開她的詩集,卻又有點失了信心,詩歌畢竟不同于文章,它是曖昧朦朧的,不講究邏輯和語意連貫的,它的語言更追求跳躍、韻律、節(jié)奏和張力。就此來說,要懂一首詩,朗誦可能是比默讀更近的徑。
于是,那個周末,午睡醒來,我把自己關進書房,大聲清了清嗓子。令我驚訝的是,開卷第一首,我一吆喝,似乎馬上就聽到了回聲,尋到了想要的答案:
《中國古巷》
水墨里
眼光向虛空一擲
夜的陰影嵌進浮雕
半堵城墻
畫個門框
給歷史留一條退路
背靠明清磚瓦
蘆葦蒼蒼
活出風骨
而我近視
不知真相在做
須臾做新一個朝代
做舊一碗清茶
以黑白鉤沉
一方閱歷的硯臺
用焦墨吆喝
不要問我讀懂了什么,我在這些詞語間先感受到的是一個男兒的豪氣,到《崩密獵廟的塌方》,又《蒙古之遠》之后,我忍不住給曹小航留言:原來,讀一個人的詩,不僅可見她的靈魂,還可見她的骨頭。”
檢察官的風骨之外,生活中的曹小航更享受做一個詩人,詩歌中有她恣意揮灑的歡欣:
……
神仙在小興安嶺會聚
甩掉黑夜的糾纏
烹調白晝的人聲鼎沸
眼里溢出藍色的湖水
頭上冒出壯闊的森林
耳朵里長出一朵朵黃花紅花白花
(《伊春的恩典》)
……
詩行之間流淌的更多的,是對俗世的關懷:
……
佛像接受膜拜
僧侶享受供養(yǎng)
流浪的人沿途乞討
沒有片瓦立足
人妖天魔地鬼神怪
在《西游記》里轉身微笑
哪兒是天堂哪兒是地獄
嗡嗡
我不人佛國的嗡嗡
只留一顆丹心
眼著唐僧悟空西天取經(jīng)
歷經(jīng)九九八十一劫磨難
在人間法庭
了斷是非凡塵
(《泰國之旅》)
留一顆丹心,歷經(jīng)磨難,在人間法庭,了斷凡塵。這是一個檢察官寫下的詩句,也是一個詩人寫下的檢察官誓言,在她的詩里,我看到了一個檢察官和一個詩人的合體。
黎巴嫩詩人紀伯倫曾說:詩不是一種表白出來的意見,它是從一個傷口或是一個笑口涌出的一首歌。在曹小航的法律專輯里,我最難忘的是寫給未成年犯的這一闋——《孩子》:
我不知道還能承受多少黑
只想關閉所有的星星
喚一輪太陽
照亮你的夜
(作者:阿朵)
責任編輯:楊博 沈彤
新聞熱線:021-6131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