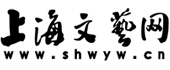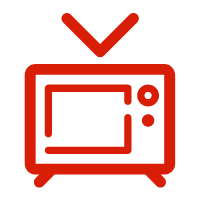小說家是有性別的——哪怕是考慮到美國人跨性別、雙性別、偽性別等多達數十種的性別分類——從生物學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是毋庸置疑的。從心理學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存在部分的偏移和偏差。那么,小說有性別嗎?刨除紛繁蕪雜的性別型,簡而言之,存在“男小說”和“女小說”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答案是肯定的:弗吉尼亞·伍爾夫的《達洛維夫人》、瑪格麗特·米切爾的《飄》、瑪格麗特·杜拉斯的《情人》、弗朗索瓦茲·薩岡的《你好,憂愁》、拉森·麥卡勒斯的《心是孤獨的獵手》與馬塞爾·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的《交叉小徑的花園》、阿蘭·羅伯·格里耶的《約會的房子》、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的《洛麗塔》一定帶給你迥然不同的性別感受——小說是有性別的,閱讀也是有性別的。同樣是寫上海,夏衍和張愛玲是不同的成色,金宇澄與王安憶文本的性別特征昭然若揭。
女權主義發展到世紀之交其實已經自覺地“鈍化”表述為女性主義,更強調性別自覺和性別立場,弱化與另一性別分庭抗禮的火藥味。也確實,不論是當今社會還是遠古、中古、近古、近代、現代社會,兩性別雜糅共生是天然的現實,敦睦好過對立,和而不同,求同存異可能是兩性別勾連的那條唯一恰適的路徑。性別革命、性別覺醒基于男權社會幾千年累積在血液里的集體無意識偶或有意無意的冒頭,出于自保,這種性別革命和性別覺醒反應過激、矯枉過正在所難免。從另一個層面來看,對于女性性別的過分強調反過來恰恰又將自己的性別置身于弱勢、式微的一方——這是一個有意思的悖論,女性性別自覺造成自我性別矮化的后果,從而達成與“男權”殊途同歸的同謀。這也就是不少事業女性如總裁、畫家、裝置藝術家、作家、詩人、導演、演員不喜歡在自己的職業、職位前面冠以一個“女”字的原因,也是我為何不大主張打性別牌,抵觸“女性寫作”、“女性表達”、“女性敘事”這類帶著強烈性別標識的標簽。
當我們強調女性的性別意識和性別自覺時,可能忽略了另一性別其實同樣具備性別意識和性別自覺。當我們捍衛“女性思維”模式和敏感、細膩、感性、較弱的邏輯性和思辨力、相對敏銳的洞察力這些“天生具備”、“生而有之”的“女性創作特質”時,不知道其實已經滑入了女性主義為之抗爭的男權意識。何況,誰說以上特質乃女性/男性作家專屬,男性/女性作家就天生缺失?有幾個女人能夠敏感、細膩、感性到像普魯斯特一樣幾乎足不出戶就能寫出窗簾外的世界?米切爾、杜拉斯、薩岡、麥卡勒斯、張愛玲的邏輯和思辨只是被大時代的迷情、天賦的才氣、濃郁的個性筆調所遮蔽,她們筆下從來不缺邏輯不缺思辨。而說到女性作家的主體性,從“我”出發去體認“我”、體認人、體認世界,幾幾堪稱天道——難道還有無“我”的創作?哪怕是被地理學、想象文學等等學科門類追認為鼻祖的《山海經》,或是《閱微草堂筆記》《聊齋志異》等志怪志異小說,《封神演義》《西游記》及至當下執“超級IP”、“頭部內容”牛耳的《盜墓筆記》《鬼吹燈》《藏地密碼》《龍圖騰》《西游傳》等等玄幻、奇幻玄之又玄的幻想文學,無不植根于現實、歷史的堅實土壤。正是由于性別意識的自覺,又清醒矯枉容易過正,我保持著對于他性別弱化、鈍化、矮化的警覺,我筆下的女性角色固然寫得活色生香,飽滿充沛,生活氣息濃郁,或高揚理想主義的大旗,我取材、提煉自生活再加以藝術改裝、創造的每一個男性角色,也杜絕臉譜化、偏平化,拒絕“紙片人”的本質一方面是藝術追求,另一方面是拒絕性別歧視。我在成為小說家之前是詩人。從詩人到小說家的轉換,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華麗轉身、應對裕如。我之所以轉身從容,可能得益于我有幾副筆法:將詩的歸詩,將小說的歸小說。我的經紀人丹飛就稱道我多面手的這個優點,因為省去了矯正、校正的麻煩。我的中短篇小說結集為《三個女人的咖啡》,我迄今創作了兩部長篇,一部《無法剎車》出版了,主題是大熱門主旋律:養老。丹飛給改名為《向著那光明》,我持保留意見;一部還沒出版,寫老上海的人間煙火、光影聲色,我起過《老城廂》《紅淚》等名,丹飛改名《弄堂深處有人家》,我覺得改得吸引人。本質上,我認可他的一切策劃、包裝、操盤,用他的話說,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我專業是“碼字”的,“碼字”是他的愛好,是他的娛樂活動,他是專業成全我們碼字的。總之,寫作上,我所有身家都交代給他了。他是暢銷書《明朝那些事兒》《盜墓筆記》《后宮——甄嬛傳》《戒嗔的白粥館》《政協委員》……的總編輯,影視劇《甄嬛傳》《王陽明傳》《匈奴王密咒》《犧牲者》《白澤圖》《蘭陵繚亂》……的IP經紀人,《狼圖騰》全版權孵化的合伙人兼副總,他也寫過電影電視劇,我相信他耀眼的成績單上可以增添關于我的一兩筆——改名后,兩部長篇明顯有了IP相。細想想,我的小說創作中何曾強化過自己的性別身份呢?犬牙交錯又相安無事,大概是兩性交駁的理想狀態。
我的這種體認有著大量同盟軍。劉慧英在《走出男權傳統的樊籬》一書中說:“我反對女性對男性的依附,我也不贊成男女兩性長期處于分庭抗禮的狀態之中,我比較贊賞西方某些女權主義者提出的建立和發展‘雙性文化特征’的設想,它是拯救和完善人類文化的一條比較切實可行的道路。”鐵凝在成為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和中國文聯主席之前是勤奮的小說家,她表達過類似觀點:“我本人在面對女性題材時,一直力求擺脫純粹女性的目光。我渴望獲得一種雙向視角或者叫做‘第三性’視角,這樣的視角有助于我更準確地把握女性真實的生存境況……當你落筆女性,只有跳出性別賦予的天然的自賞心態,女性的本相和光彩才會更加可靠。”身為美國“女性主義批評”創始人之一的伊萊恩·肖瓦爾特對于超越性別局限進行反撥:“想象力逃脫不了性別特征的潛意識結構和束縛……不能把想象力同置身于社會、性別和歷史的自我割裂開來。”——如何基于性別事實,又不囿于性別藩籬,是寫作者需要長期摔打歷練的課題。這個過程中會有隱秘之歡,也會有齟齬之痛。如果說我和我的小說有性別的話,其性別不是女,是“我”。(作者:陳佩君)
責任編輯:楊博 沈彤
新聞熱線:021-6131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