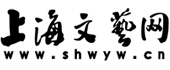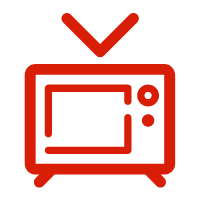楊瀾采訪余光中的提問:
1)楊瀾:其實我們看您的這個人生的經歷方面,我們覺得其實并沒有遇到過特別大的困頓,好像您看比如說家庭也很美滿,很安定,那生活呢,教書、寫詩、寫散文、寫評論,也應該是人們想像的那種比較安定的一種生活,但是您為什么卻說,您說我寫作是因為我失去平衡,心理失去保障,而心安理得的人是幸福的,繆斯不會去照顧他們?
余光中:一個人不能光看他表面的職業跟家庭,他內心有很多心魔,內心世界可能很復雜,可能他的愿望并沒有完全達到,那就不是表面上看得出來,同時我早年至少在二十一歲那年離開中國大陸,那對我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因為我的好朋友都忽然不見了,然后我投入一個陌生的地方,要重新來過,那么而且一個人到了二十一歲,記憶已經很多了,所以這件事情念念不忘,也成為我一個中國結。
2)楊瀾:我覺得您身上的一些氣質跟人們原先所想的那種詩人的氣質有一些看起來似乎矛盾的地方,我們印象中的詩人,要么像李白那樣放蕩不羈的,但是您在自己的行為處世上都是非常的嚴謹的,或者人們想到詩人可能是非常浪漫的,但是您與您的太太可以說是白首偕老的。
余光中:當然如果一個詩人浪漫的話,他不會在接受訪問的時候表現出來。我翻譯過王爾德三本喜劇,王爾德就對一個朋友說,因為朋友問,問他這個問題,他就說,我過日子是用天才,我寫作呢是靠本事,那意思就是這個過日子比較重要,我是覺得應該反過來,如果有天才要完全用在寫作里面,至于過日子呢,將就過得去就可以了。
3)楊瀾:當您的女兒們還是在中學里的時候,您寫一篇文章叫《我的四個假想敵》,就是想像將來有哪個男孩子要把您的一個個女兒娶走的話,您跟他們將怎么樣的對立,那我想今天這些假想敵都已經成為真的敵人了,您跟他們相處的怎么樣?
余光中:那也沒有,可以說虛驚一場,因為后來只有兩位結了婚,現在女性很多都很獨立,那么比較晚婚的很多,總之四個女兒只出嫁了百分之五十而已。
4)楊瀾:所以您現在著急要找另外兩個假想敵了嗎?
余光中:我倒也不著急,我覺得那是她們自己應該決定的事情。
5)楊瀾:您到大陸去做了那么多次的演講,和這個跟同行的探討,覺得哪一次對您的印象比較深呢?
余光中:我前年在那個長沙的岳麓書院演講,我當然覺得這是很隆重的一件事情,因為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點,這個朱熹、張栻講學之地,怎可造次呢,所以那天我去了,是九月底,那么秋雨綿綿,也蠻涼的,而且,而且這個雨后來就下得更大了,那我在那個堂上講,而臺階下面的院子里面,有差不多四百個聽眾,全部穿了,帶了雨帽穿了雨衣,我覺得也很感動,所以我再三呼吁老天爺,不要再下去了,我而且我當場說,我說去年也是這個時候,余秋雨來講,聽說也下雨,不過那他不能怪老天,因為他叫秋雨,一個是秋天來,天上要下雨,我叫光中,對不對,我應該是陽光之中,不過除了鎂光之外,今天天色很暗,也下著雨。
6)結尾:縱觀余光中的一生,可以看出其中有不少的輾轉和漂流,從江南,到四川,到臺灣,到美國,到香港,最后再回到臺灣,有的時候是痛苦的逃難,有的時候是主動的選擇,這使他的詩歌題材也顯得相當的豐富。
在他的辦公室外,是美麗的西子灣,海那邊就是他曾經居住過的大陸和香港,有人說"時運不幸詩人幸",也許就是這一水之隔造就了余光中許多膾炙人口的鄉愁詩,不過則有更多的人希望,有朝一日余光中不必將這鄉愁進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