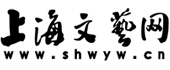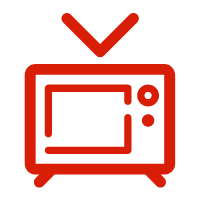從《山路十八灣》唱紅說開——與著名詞作家佟文西一席談
孔鴻聲
“這里的山路十八彎,這里的水路九連環。十八彎彎出了土家人的金銀寨,九連環連出了土家人的珠寶灘。彎彎環環,環環彎彎,都繞著土家人的水和山……”。一首《山路十八灣》從創作到唱紅,整整經歷了十個年頭。俗話說:“十年磨一劍”,確實是道明了歌詞創作之路跋涉的艱難。
今年6月中旬,著名詞作家佟文西陪伴他的兩位“忘年交”朋友來上海東方藝術中心舉辦“獨唱音樂會”,在他離滬前夕之夜,在他的下榻賓館之處,筆者與他作了一番有關歌詞創作方面的交談,由頭就是從《山路十八灣》說開的……
多鉆研理論,為作品注入能量
筆者:聽說您以前是注重寫詩的,在《湖北日報》、《長江文藝》、《布谷鳥》《詩刊》等省級以上刊物上發表了不少有影響力的詩作,在詩界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同時還時常發表一些小說、散文等作品。怎么突然想到轉身從詩界步入詞壇,鉆研起歌詞寫作了呢?
佟文西:那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第一春,市里、省里辦了好幾起“歌詞創作學習班”,要求能多創作一些歌詞作品。我寫過對口詞、快板詞等,還就是沒寫過歌詞。參加了“歌詞創作學習班”后,根據學習班提供的一些“樣板歌詞”,就開始學寫起來,在學寫的過程中,我感覺以前自己寫的好多詩歌,如果從形式和語言上作一些調整和修改,不就是很好的歌詞嗎?于是就試改了幾首,想不到竟得到了同行們的認可,有些歌詞還被發表了出來。這樣一來,我就把以前創作的詩歌,能改成歌詞的,就用心地進行再創作,一星期能改成十多首。這些歌詞大多數都被發表了,好多歌詞還被譜上了曲子演唱了,并在一些征歌、演出中獲獎。那幾年,可以說是我的獲獎高峰期,前前后后、大大小小拿了上百個獎。此后,我的創作就從詩歌轉入歌詞,一門心思地開始注重起歌詞創作了。
筆者:幾年中就獲得了那么多的獎項,您是否認為寫歌詞比寫詩容易?所以您就來個“華麗轉身”,棄詩重詞,開始與歌詞“交朋友”。
佟文西:卻卻相反,相比之下,寫歌詞要比寫詩難,因為寫歌詞要受一定“框框”的限制,比如創作的格式、字數等,沒有寫詩那樣隨意和放得開。真如喬羽老先生所言:歌詞好寫,要寫好難。當時自己連個大專的文憑也沒有,文學基礎實在太淺,因此我很想讀書,想到某個地方好好地去學習一下。所以,當1986年湖北省文聯把我從荊州沙市農藥廠調到《長虹》詞刊當編輯時,我向領導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一旦有讀書的機會,希望領導能成全我。
說來也巧,到《長虹》詞刊當編輯不到一年,天津音樂學院首開“音樂文學”大專班,我就向文聯領導要求去讀書,雖然當時編輯部人手也緊張,但領導沒有忘記對我的允諾,同意我去讀書,并給我報銷了一定的費用。
全脫產進入了天津音樂學院,通過在“音樂文學”大專班兩年的系統學習,確實使人受益匪淺,首先是在學習歌詞創作理論的同時,還對歌劇、戲曲、音樂劇等類型的作品進行了研究分析,進一步了解和掌握了“音樂文學”創作范疇,擴大了歌詞創作的學習視野。二是對歌詞創作審美藝術的把握,有了深層次地提高,能從理論上對自己以往創作的歌詞作品,清楚地劃分出一、二、三流的作品界線;對他人的歌詞作品,能分析出那首是值得學習的,那首是值得點贊的。三是為以后工作能力的提高和創作水平的提升,夯實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為以后的職稱評定等創造了有利條件。所以我認為:對一個文藝創作者來說,全面地、系統地進行文藝理論學習和鉆研,是為作品創作的提升,注入了極其充實的能量。
在臨近畢業時,天津音樂學院要我留校,同班同學韓偉(《打起手鼓唱起歌》詞作者)邀我去北京發展,但都被我拒絕了,我懷著一顆感恩的心,仍然回到了湖北省文聯,繼續擔任《長虹》詞刊的編輯。
多深入采風,為作品強身健體
筆者:在您的作品中,生活氣息的反映特別濃厚,山水畫面感特別清晰,一邊聽著歌聲,一邊腦海中就會出現歌詞中的動感畫面。這在《山路十八彎》、《喜事多》、《一把菜籽》等作品中都能充分地體現出來,您在創作中是怎樣去做到這一點的?
佟文西:這要歸功于采風活動。我對創作采風活動特別感興趣,是一個“逢山必爬”的人,直至現在,只要有采風活動,我一定會積極參加的。我從事歌詞創作已經有40個年頭了,參加過無數次的創作采風活動,走過了祖國的好多山山水水,每到一處都感到那么新鮮、那么親切,那么有感情,創作靈感就會由然而然地迸發出來。
每次出去采風,同事們都說我是創作最勤奮的人,因為我每到一個地方采風,都看得很細、問得很廣、挖得很深,所以掌握的素材也特別多,創作起來也就特別顯得得心應手。其次,我的采風創作,不是那么寫一、二首完成任務交差式的創作,而是喜歡一組、一組地寫,把自己采風所獲得的素材盡量地轉化為作品,最終把最好的作品拿出來。
就拿寫《山路十八灣》來說吧,1990年夏天,我和同事們一起去鄂西采風,一路走一路觀察,一路請教一路當小學生,去了十多天,領略了土家的原始風情,欣賞了好多土家人的民俗歌舞。我們在欣賞中不斷地去挖掘這些原始歌舞的“魂”,只有把這些原始作品中的“魂”提煉出來,才算是真正體驗和反映出采風的精髓。通過一路采風,我先后寫出了《擺手舞》、《巴山舞》、《喊山歌》、《烤土豆》、《土家山歌》等歌詞,但總感到還是沒有寫出土家風情的真正精髓。我和另一位作曲家繼續坐車向深山里進發,清晨的山霧也是很迷人的,那一座座土家人的吊腳樓隨著山霧的飄動,一會兒模糊一會兒清晰,很有韻味,我當時就在車上寫出了腹稿《霧海中的土家寨》。當山霧散去天空放晴,汽車一個轉彎時,我猛然地從車窗中發現了山下這一驚人的畫面:大山之中彎彎環環的山路,清江河邊環環繞練的水道。創作的火花一下子就閃耀出來:“這里的山路十八彎,這里的水路九連環”,抓住了這一創作之“魂”,接下來的創作就順理成章地出來了。當初這首歌的標題叫《土家的路與歌》,后來在參加一個創作大賽時,改為《太陽之子》,1999年上“春晚”時,閆肅老先生將它改為《山路十八灣》,由李瓊首唱而響遍大江南北。
所以說,我們的歌詞創作也不能坐在家里,憑著一些資料“閉門造車”,一定要深入到生活中去,腳踏實地地認真采風,不能走馬觀花。如我去新疆采風,去了一個多月,寫了95首歌詞,把采風中所看到的、聽到的都寫了出來,僅以《龜茲美女》為題的歌詞就寫了17首,反反復復地進行比較,最后拿出自己最滿意的作品。我認為:通過采風可以了解和掌握書本上、資料中所沒有的東西,而這些東西又卻卻是歌詞創作中所不能缺少的,這就是生活!采風是一種生活的體驗,通過采風,用學習和掌握到的第一手素材,經行加工后增添到那些“弱不禁風”的作品中去,為它們強身健體而豐滿起來,成為一首真正的好作品。
多溫故求新,為作品延年益壽
筆者:綜觀國內詞壇,每年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首歌詞問世,而真正能唱起來的可說是寥寥無幾,有些詞作者寫了一輩子的歌詞,都沒有一首能在舞臺上唱響。據說您四十年來也寫了近5000首歌詞,各種獎項也拿了500多個。您作為著名詞作家、詩人、國家一級編劇、中國音樂舞蹈家協會副主席、中國音樂文學學會常務理事、中國音樂家協會、中國作家協會、中國電視音樂研究會會員,但能像《山路十八灣》這樣唱紅的作品也不多。怎樣才能讓歌詞作品多多地從抽屜里走出來,插上音樂的翅膀而唱響在社會上呢?
佟文西:這個問題說起來很復雜,涉及到諸多方面的因素,一下子也是個很難解決的問題。但從詞作者本身而言,我們在創作作品時,就應該慎重,每寫一首作品都要精打細磨,不要粗制濫造,因為你自己在創作作品時,沒有從人民大眾的需求出發,所以人民大眾也不會來眷顧你的作品,這是很公正的辯證法。所以我給自己歌詞創作定了4條規定:一是要出新、二是要寫準、三是要有美感、四是要有情感。特別是情感最重要,一首作品如果體現不出情感,情感游離在作品之外,再怎么寫也是不會成功的。
其次,對自己已經寫好的作品,要經常地“回頭看”,溫故求新,讓躺在抽屜中的作品,重新走出來。我現在退休了,雖然新作品還在寫,但其創作的熱情和沖勁,比年青時是大大地減弱了,必竟年歲不繞人嘛,所以新作品問世也少了。但我并沒有閑著,目前我注重做的一件事是就把以前寫好的、而沒有能用上的上千首作品,再認認真真地細細琢磨。有好些作品因受當時的創作思想、創作水平市場需求或時間倉促等多種因素的局限,并沒有很好地進行打磨,寫得有點粗糙或簡單,使它們沒有能走向社會而被埋在“土”里了。這些作品中無論是題材或內容,好多都是能夠被“挽救”的,我就把它們從“土”里挖出來,進行認真細致地再加工、再修改,是金子總要讓它們發光吧。如最近提倡寫一些中國神話題材的歌詞作品,而我在好幾年之前就把中國的所有神話故事寫成了歌詞,但當時沒有發表和演出的“市場”,這些歌詞就被埋進了“土”里。現在需要了,我就把它們“挖”出來,重新加工潤色后就被采用了。
一個搞歌詞創作的人,不可能使自己所創作的歌詞都能發表和演唱出來,這也是不現實的。但我認為:因為沒有發表或演唱,這些作品就顯得一無是處而把它們扔在一邊不聞不問,這就是自己對創作不負責任。這好比自己生的孩子,有病了或那兒不舒服了,就應該為他治療,讓他康復起來、成長起來。所以,對以前所創作而被擱置在一邊的作品,要經常地去“溫故求新”,為它們延壽益年而創造條件。
從外表上看,佟文西不像是一位已經74歲的老人,仍然是那樣精神矍鑠、那樣思路敏揵、那樣談笑風生,與筆者交談了一個多小時并不顯得吃力,因為對歌詞創作他有太多的感悟……
責任編輯:楊博 沈彤
新聞熱線:021-61318509